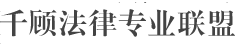“立法滞后”在笔者看来具有积极意义。金融犯罪的认定应该以金融违法行为为前置条件,这是金融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刘宪权教授认为,“立法滞后”是我国金融犯罪法律层面的一大原因,“相关刑事立法滞后,使得金融犯罪的规制始终落后于金融犯罪的发展变化,一些已严重危害国家金融秩序的犯罪,因为无法可依而畅通无阻、嚣张蔓延”。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金融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法定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刑法还尚未将某种行为纳入立罪考量,又何来犯罪之说。其次,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社会危害性来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罪的本质是应受刑法惩罚性。尤其是在行政法规还没将某些金融行为纳入行政违法的范围,提前以刑法介入有违启动刑罚的初衷。这里所言的金融犯罪的入罪应该同时包含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双重违法属性,也就是说只有在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中对某行为作否定性评价并配置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指引适用规定时,该行为方可进入刑法的视野。金融刑法保护的法益应该以金融法规保护的法益为限,我们的立法者对此的态度也是以二次违法性的“双违反”来起到兼顾金融创新与金融秩序利益平衡的效果。
金融刑法的扩张是指:在立法层面将一些不应受刑罚惩罚性的金融违法行为纳入金融犯罪圈,在司法层面上积极地采用类推解释和兜底性刑法条款以对金融违法行为实施严厉打击。前文刘宪权教授的观点似乎与金融刑法之扩张相近。在实践中,一方面有时出于打击经济犯罪的严峻形势以及我国金融刑法“家长主义”压制型立法的特性,在传统国家本位主义理念下片面强调维护国家金融垄断地位和国家金融管理权,把金融刑法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与安全放在利益追求的首位,把维护投资人利益的价值追求滞后。一旦行为人在客观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经济损失又是经济犯罪、行政犯罪等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指标,就算刑法没有明确的入罪标准之规定,行为人也可能会落入刑法规制的犯罪圈,采用兜底性条款对其进行归责。此类立法极度表明了在金融市场活跃的今天,金融刑法更倾向于“风险刑法”的理念,由此引发的就是刑法扩张的危机和对刑法谦抑性的挑战。比如我国1997年《刑法》先规定了证券犯罪,而之后颁布的《证券法》才就证券犯罪作出具体规定,由于二者内容上存在出入,在后来的《刑法修正案》中又对证券犯罪做了进一步修正。又如《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修改了刑法第187条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删除了“以牟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删除了资金用途的限制性规定等,实则扩大了刑事打击范围。
另一方面,刑事司法解释扩张了部分行政法规的原意,导致处罚面扩大、入罪门槛降低。比如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犯罪主体的界定,在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界定上存在争议。根据2012年两高《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援引《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基础上,首次将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纳入“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范畴,这类人群包括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员、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的人员。这一解释实质上放弃了对行为人是否采取窃取、欺骗等非法行为手段的考量,而是将证明重心放在了特定人的特定身份或人物关系上。虽然针对该主体规定了“有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除外条件,但是这一法律解释技术也并没改变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犯罪主体范围扩大的事实。刑法司法解释扩张了前置性行政法律法规所列举规定的行为对象的范畴,通过能动性的解释,将某类人群纳入刑罚规制范围,相当于在创制行政法律法规,突破了司法解释权力的该有的界限。长期以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似乎形成了强大的思维定势,只要涉案行为对社会危害较大,就应当寻找近似的刑法条文对其进行归责。由于构成要件中,刑法解释具有天然的延展性与包容性,这种思维模式极易导致司法解释过度介入,产生刑法不当干预非刑事领域的种种司法怪像。
这里要把预防性立法与金融刑法的扩张相区别。所谓预防性立法是指立足本国金融发展的现状,回应金融市场未来的风险控制,在充分调研分析新型金融犯罪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将部分鄞受刑罚惩罚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纳入立法范畴。预防性立法以金融法律法规作为探路石,这是与金融刑法扩张的显著区别。预防性立法是顺势而为,对于抑制新型金融犯罪起到打早打小的效果,将金融犯罪控制在萌芽阶段。而金融刑法的扩张是刑法的过度介入,是在面对金融犯罪时出于打击的实效和维稳等要求,立法上人为地将犯罪圈扩大,并延伸刑事司法打击面。
作者:林 都
编辑:邱美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