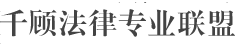| 为清楚阐释语词或数理逻辑符号通过其使用规则建立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曾经选择如下的对比:谁要声称其是自我意义的单独承载者,他就与国际象棋选手一样:后者在创设国际象棋角色时,建立起了其面目可憎的涂彩女王,她看来既恐怖又使人厌恶,以至于要将对手的任何角色从场上驱离。1985年,Jakobs教授在刑法理论中提出了敌人刑法的概念。对此,他的对手稍后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他太可怕了,在他的结论里,他想要驱走自启蒙时代以来所有法治国家的成就。接下来的论述将完全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将视角从作为定语的自我特性描述转向于存疑的敌人刑法概念的应用,以查明这一概念是否真的拥有那样的“魔鬼般的能量”[1],或者是Jakobs的那样批评者在使用相同角色来艰难地进行别的游戏,或者说仅仅是以别的角色来进行同一游戏。 一、作为事实的敌人刑法 (一)描述 在对法益侵害前阶段的犯罪化进行研究时,Jakobs诊断出了对市民——自由刑法的侵蚀倾向。[2]他根据四种征状来证立这一得到多数人认同的分析。 从建立在责任原则基础上的市民刑法向斗争立法转变的过程,已经证实了某些法律具有“斗争法”的特征——正如恐怖主义对抗法、恐怖主义斗争法、性犯罪和其他危险犯罪行为斗争法,非法毒品交易及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斗争法,欧洲司法(针对严重刑事犯罪的强化斗争法,或对抗经济犯罪的第一法案与第二法案)在“国际法的基本文本里”,“正统法律概念的属性所采纳的”目标设定——“斗争”“对抗”[3]——清楚地表明,对恐怖分子或(有组织)犯罪的惩罚,实际上成了追求警察目标的手段,即制造安全。[4] 对立法者采取的这种命名方式,我们虽然可以认为它在修辞学上太过草率而不用理会,它只能证明立法上的某种随意。[5]但在Jakobs看来,有一种更好的实体刑法在这里教导我们:那样一种与犯罪作斗争的规则其特殊性在于行为原则在其中被丢弃——为了安全的目的,要么通过对行为人的刑罚执行来将犯罪人“对立化”[6],比如保安监督;将犯罪行为实施前的前领域犯罪化,尤其是在私领域完成的实质性犯罪预备,比如对犯罪分子或恐怖组织的教育。在其中,根本没有证实存在着真正具有可罚性的行为,甚至连直接的未遂也不能得到证实,只是刚刚才被计划。与此相对,仅当单个行为人直接着手去实施犯罪行为时才是可罚的(《刑法典》第22、212条)。这样对待顺从者的国家,已经不再停留在市民刑法的层面,而是建立起一种不再倾向于自由领域、不再要优先保护法益的新法律。[7] 此外,对刑法的侵蚀还体现在程序性保障的解体:这始于刑事诉讼法第81条a款规定的受容许的强制抽血检测及其他身体强制干预,它与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款及基本法第104条第1款第2项正好冲突[8];更为深入的侵蚀是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款规定的受容许的监控,秘密侦查(刑事诉讼法第100条c款);最后是法院组织法之引导法(EGGVG)第31条对一定调查嫌疑人的接触封锁。[9]审前拘留有时只是在服从于法益保护。[10]从2001年9月11日起,这一点被进一步补充为通过战争来追捕犯罪。[11]所有这些措施,虽然“不是在法律之外发生,但是,被告却出现在了法律之外,因为其遭受干预、权利也被剥夺:国家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取消了其权利。”[12] 人们现在能够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此类措施所指向的要么是抽象危险犯,要么是保护社会风气的犯罪或对优先法益的侵犯。第一种情形关系到的是比如建立犯罪组织或恐怖组织,或者谋划共同犯罪,相似的还有酒后驾驶或私藏武器级的钚。立法者认为此类行为在客观上极其危害,它们无需行为人进一步意志就可以侵害到法益。行为人的信念无足轻重,立法者就是在无视个体的、内心的区别。尤其是如法律对在恐怖组织基地停留要给予刑罚的规定所表明的,此种行为涉及完全相反的情况:一定技能的学习本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性,立法者在刑法典第89条a款中是对信念态度规定了刑罚。 但是,此类行为也可能是因侵犯到优先法益而受到惩罚,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恐怖组织的存在对社会确实是“弥散的威胁,潜在的不安全影响”[13]。在市民刑法体系内同样可以讨论对公共安宁、公共秩序或者说对法和平的侵犯。对此种法益的侵害或其他类型的威胁(刑法典第241条)[14],以实施犯罪行为威胁(扰乱公共安宁)(刑法典第126条第1款)或煽动种族仇恨(刑法典第130.131条)都要被科处刑罚。刑罚不以犯罪人的危险性为目的,而是要惩罚接下来发生的对公共安全的侵犯,这只能表明在犯罪预备中“刑罚比例递减的前置化”[15]。[16]首先,不仅是刑法典第129条a款、129条b款对接受恐怖组织教育的人规定了与罪责原则限制功能不相符合的刑罚尺度(刑罚幅度始终与身体伤害的严重性相对应![17]),以及在程序保障方面对其的限触[18],都表明了相反的内容,即在这里,惩罚的并不是对公共安全的侵犯,而是应该被威慑且首先应该被排除的危险。 (二)阐释 在Jakobs看来,上述规定指出了“从含有规范效力的刑法,即通常所说的罪责刑法,向在受到危险威胁时要作为保安处分法的刑法的转变”[19],在其中,罪责原则与行为原则被丢弃,以此来对抗危险。[20]刑法一词原本的含义也因此而不复存在。[21]更有甚者:那样的一种法律没有将服从它的主体视为市民,而是视其为对值得保护的法益潜在或现实的敌人。 Jakobs认为,在“内部的市民领域”[22],个体是通过他“免受控制的权利”[23]而被确定为市民。只要拥有免受国家干预、受到保护的私人领域,市民就始终是市民。当他的内部事务成为刑法上可以被犯罪化的对象时,这样的私领域就被剥夺了,他就不再是市民。该内部事务不仅包括霍布斯所说的思想,还包括衣服、住房及财产之外的、全社会的和睦交往。“没人因思想犯罪”的定理,只要不超出与他人的和谐行为,就只是在私人领域的特殊情形的市民法。外部空间首先从非和谐的社会往来开始。在此种意义上,预备犯罪的社会关系仍然只是私人的内部事物。 市民刑法必然导致的结论是,受到了刑罚的只应是外部行为,而不会是内部事物。国家绝不能因行为表现出内部事物而处刑。市民只有实施了破坏性行为时才能成为犯罪人。“无论如何,对内部事物的追问只应被允许用于解释已经受到破坏的外部状况”。[24]否则惩罚最终是透过实际上不引人注目的行为来瞄准行为人的内部状况,它作为诠释介质将那些不引人注目的行为解释成为引人注目的行为。正如属于私领域的行为人内心思想、打算实施犯罪的约定都不应受刑法干涉。因为对由约定产生犯罪预备的知的本身,不比对单独作案者大脑里的犯罪计划的知的破坏性更少。[25] 犯罪行为的前置,并不是将对外部的破坏性犯罪化,而是通过把行为人内部状况解释成对法益的危险,从而将完全不存在问题的态度犯罪化。当在实体刑法上,刑法典第30条参与的未遂中私人领域内的约定被定义为犯罪,刑法典第129条a、第129条b规定的恐怖组织教育也被设置了刑罚[26],市民也就不再是作为市民,而是作为敌人被对待,因为在外部还没有表现出破坏性态度的情况下,这些市民的内部领域已经被认定。[27]这样的规则不是服从于市民自由领域的安全目的,而是在致力于防止一定法益将来受损的危险,因此,Jakobs将其称为“敌人刑法”[28]规则。 (三)分析 Jakobs通过法益论与契约论建立了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对立的理论基础: 法益论将刑法首先理解成是保护法益的工具[29],刑法相应地是对侵害法益的制裁。法益论本希望通过对刑罚尺度的限制来限定实质刑法[30]:法益的义理应该给立法者设定严格的边界,即到底允许立法者去惩罚什么。尤其是对纯粹侵犯习俗禁忌、品行及道德的惩罚,因此而是不被允许的。[31]在Jakobs看来,那样的意图却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因为,为了法益保护的目的,刑法扩张到了没有边界的程度[32]只要被认为是对某种法益的危险,就会被认定为犯罪。对法益的潜在损害证立了既遂的前置,且由此证立了前阶段的犯罪化,“由此,危险开始的时间点便潜在的、没有边界地被前置”[33]。行为人“仅仅是危险的源头,换言之,是法益的敌人”[34]。在市民刑法的名义下,法益论却在结论里威胁要将每个犯罪人作为法益的敌人来对待,它披着市民刑法的外衣,实际却成了敌人刑法。法益论者虽然将所有犯罪人都称为市民,但仅仅是在名义上,因为它没有区分市民和敌人,混淆了不同领域的规则。 与此相对,契约论,尤其是卢梭和费希特的契约论,具有将每个犯罪人解释成为敌人的倾向:犯罪意味着对社会契约的解除声明。由此,卢梭和费希特将每个犯罪人称为敌人,并且否认其作为市民的地位。因为行为人的犯罪,宣布了社会成员之间订立的契约无效,故他不被允许享有该契约更多的好处,且也不能再与其他人继续生活在法律关系之中。因此,卢梭将那些侵犯社会权利的人称为敌人[35]。对费希特来说,犯罪人应该接受的不是刑罚,而是安全措施。 在霍布斯和康德之后(霍布斯区分了反叛者中的敌人与市民中的犯罪人,康德保留了普通犯罪人的人格体地位,只将原则性偏离者解释成敌人)[36].Jakobs认为,犯罪人必须继续地成为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载体。违法者同时具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再次与社会达成的和解来完成赎罪。因此,与“将犯罪人定义为法益敌人”相反,Jakobs“将犯罪人定义为市民”。[37] 市民刑法不是要用来抵抗危险,而是要维护市民应当遵循的规范的效力。[38]犯罪不是对法益的侵害,而是对“法律性的侵害”[39]市民的犯罪行为,意味着对“规范的否认,对规范效力的侵犯”[40]。由此,犯罪不是消解社会的标准化,而仅仅是使社会的标准化变得混乱。[41]刑罚将犯罪人的行为原则认定为无效,从而宣告在规范违反行为中所表达的看法不具有效力,确认规范不可变更的持续有效性。[42]只要规范在对犯罪人的科刑中被实现,该规范的社会效力便没有被犯罪人否认。它的真实性在刑法上的矛盾中“反事实地得到了维持”[43],也因此能够维持对(潜在的)犯罪人及(潜在的)被害人的行为指引功能。[44]故犯罪与刑罚是“象征性交互行为的工具”[45],它们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由此,在Jakobs的意义上,刑罚是交往程序的要素。作为规范违反的对立面以及由此反事实的规范确证,刑罚意味着“行为因其含有规范违反的意义而被边缘化”[46]。只要犯罪人的行为被反对,他就仍然被承认为人格体。“犯罪人仍然是法律上的人格体。”[47] 但是,市民的法律性的此种条件同时表明了它的边界。[48]因为刑罚并不仅仅意味着、同时还要产生对心理的某种影响,即威慑(消极的一般预防),以及对身体的某种影响,即安全(消极的特别预防)。它通过强制来达到那样的效果。强制使得犯罪人非人格体化。[49]刑罚以此作为首要目的,犯罪人也因此不再被承认为是人格体。黑格尔已经对消极的预防性刑法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反对意见,在消极的预防性刑法中,人们不再将人作为一个人格体——人们可以提出规范要求的人格体,且可以期待其源自理性洞识的承认——,而是将人作为一条狗来对待,人们对其举起了木棒[50],且在保安监督(刑法典第66条、第66条a、第66条b)中,人们对待具有致重大犯罪习性的违法者,明显地更像是人们必须自保以免受其害的某种危险或是一条狗。 如果忽略掉哲学上的伴随现象,Jakobs在此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现在有问题的是,他认为,在一定情况下将那些明显是完全或部分地不愿意前往共同的法定状态且因此持续威胁到国家规范有效性的国家中的主体作为敌人来对待是必须的。规范必须被实际地遵守,而不仅仅是理论上有效,社会成员才能够以其作为行为的方向。[51]如果人们对规范效力的期待被频繁地改变,规范就不再能为市民提供行为指引。因此,至少在通常的情况下,法秩序必须得到实现。如同规范的有效性,犯罪人的规范忠诚也需要有一定的、认知上的、最小程度的证明[52],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提供了那样的证明。[53]谁拒绝做出保证,即在认知上要承认其所处社会的规范——比如,通过反复地严重违反法律来表示拒绝——,法律就必定不会将他再作为市民——能够以规范来自我指引的理性人——来对待,至少是要部分地将他作为危险的敌人来对待。刑罚因此成为对敌人的回应,它应该剥夺他所有的手段,正是因为那些手段他才变得危险。[54]国家与其市民的特定联系,主要是“仅仅对客观行为的反应,而不是对纯粹预备的反应”[55],因此是不相称的。在Jakobs看来,此“敌人刑法的丑陋一面”[56]至今仍没有完全消除,正如在个体那里,在认知上并不提供对市民的——人格体的行为的最低保证,表面上则对法律表达了持续或明显的轻视(就此而言,那些否认这类规则的恐怖分子仅是极端个案)。在某种意义上,犯罪人是回到了自然状态,因为他事实上完全没有承认规范。从他的角度看,没有法律作用于他,起支配地位的是某种形式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者决定何种规范有实际效力。[57]因此,法律存在两种理念类型:“市民刑法是所有人的法律,敌人刑法是反对敌人的人的法律;针对敌人仅需身体强制,直到发动战争。”[58] Jakobs主张清楚区分两种类型刑法的概念:对规范上的犯罪人,刑法是一种否认,是对损害赔偿的强制要求;对于敌人,刑法是一种安全措施。[59]因此,对于市民看重的是其实施的行为以及直接着手的企图,对于敌人则纯粹是基于安全理由而实施身体强制。从这样的概念差异可知,为了将市民中的犯罪人始终看作是法人格体,人们应将用作“敌人对抗法”[60]的敌人刑法从市民刑法中筛选出来。并非每一犯罪人都是法秩序的根本对立者,“在法治国的层面,在普通刑法中同时存在着的、敌人刑法的绳和粒很难被无视地在被施行,就是一种恶。[61]市民刑法受到的这种慢性侵蚀,敌人刑法过多地适用于市民,这些都需要被避免。[62] 二、作为规范概念的敌人刑法 接下来本文分析对敌人刑法的批评,特别是在规范理解层面提出的批评:一方面将对敌人刑法的观念在概念上予以明确化,另一方面则要准备回答敌人刑法作为调节性观念的合法性问题。因此,这里将继续搁置对敌人刑法实践效果的讨论。[63] (一)敌人刑法与纳粹思想在精神上的亲缘性 观点:Jakobs敌人刑法的观念不仅被批评是在自相矛盾、不具可行性或是纯粹无意义,还被他的论敌从道德层面进行了谴责和批评[64]一些批评者称,Jakobs是“精神上的纵火者”[65],他的敌人刑法是在表达极权主义思想。[66]将他推到纳粹思想近侧的人并不少(比如他的学生Pawlik)[67]:Jakobs的敌人概念与Mezger提出的“共同体的对立者”“反社会的”及“没有存活价值的生命”的概念具有历史性的相似[68]在从纳粹发展起来的犯罪人类型学说之后,具有再社会化可能性的普通犯罪人与恐怖分子的对立,听起来就像是为了“具有历史意识的法律人”而存在。[69]敌人刑法的话题,当然会引起对它与“Carl Schmitt的政治敌人概念是精神层面共犯的担心”。[70]Jakobs本人反对那些认为他使用的“敌人”术语与Schmitt的具有实质亲缘性的说法,但是,他的反对并没有阻止住那些批评者。[71]与此相反,Pawlik“不会对自己提倡要捍卫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Schmitt的主张会引发论战感到太遗憾。”[72] 辨析:“纳粹的”这一称号仍能引起现实争议,不过,对那些基于如下理由的批评者来说,这一称号本身却并不是充足的理由: (1) Jakobs并没在任何地方提到种族意识形态。[73]要去寻找Jakobs对Schmitt反犹言论[74]的肯定,或对保护“人民生命权”[75]的元首的赞歌,只能是徒劳无功。 (2)若是认为Jakobs赞同针对具有危险性的习惯犯的立法传统及关于保安处分的立法传统,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尽管传统立法上存在保安监督的规定,但是,Jakobs暂时只是在着重强调它的效力,且将之作为疑难问题而提出,他并没有去问及它的实施。有问题的,毋宁说是时至今日保安处分法仍是刑法典的一部分。因为刑法典与保安处分法的混杂——Jakobs要求对此进行严格的分类——正是纳粹的法意识形态想要立法的。[76] (3)敌人刑法虽然是行为人刑法,但与行为人类型学说不同。发表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法与立法手册”中的“法治国”条款中,Schmitt将行为人刑法与行为刑法归入到自由法治国的规范思想,且据此与纳粹刑法区别。[77] (4)“敌人”或“例外”概念的使用,不会因它的提出者道德品行恶劣而有疑问。一种概念,要么是适当的,要么不适当,但其本身却不是不道德的。虽然Schmitt在其敌人概念及例外状态概念里已经表明对纳粹的奉迎,但那并不是直接且显而易见。这单独指出了那些受Schmitt哲学积极影响的人的实际情况:否则人们必须怀疑AlexandreKojeve或犹太哲学家及犹太教经师具有“极权主义思想”[78],谴责他们是纳粹主义的“精神共犯”——在一封致Schmitt的信函中,Rabbiner自称为“纯粹犹太人”[79],因此是Schmitt的纯粹的敌人。 (二)敌人刑法的不必要 【观点】即便敌人刑法观念本身不具可谴责性,但也没有必要将其现实化,因为没有敌人刑法,国家也已经有了防御。国家已经拥有被证明过的、针对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手段。[80] 【辨析】此种论点存在缺陷,因为它是反事实的:Jakobs是认为,那样的防御型国家已经将敌人刑法要素整合进刑法典,只是并不那样去称呼它。因此,大多数论者与Jakobs一致的是,刑法越来越带有危险防御法的特征,安全利益居于主导地位。[81]如果没有敌人刑法要素,刑法是否仍能防御,至今为止仍然是假想推测;Jakobs根本没有主张去拓展敌人刑法要素。 (三)描述性要素与规范性要素的混杂 【观点】与Jakobs所声称不同的是,他本人的论述是描述性的[82],且并没有在此问题上说哪些人是法应该视为敌人加以对待的,他说的是谁在被法作为敌人来对待且从中会对将来产生何种影响[83],在最近的论著中,Jakobs对敌人刑法概念的使用不再是描述性,或只是完全批判、公开谴责性的,而是在规范性地使用它。在“使人震惊的思想”中,通过歧义性,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免疫,因为人们并不知道Jakobs是否已经使敌人刑法概念合法化,还是仍然只是在描述它。[84]因为Jakobs是“黑格尔主义者,且因此是整体论者”[85],他对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的概念不能被清晰区分。 【辨析】与此相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Jakobs本人对被称为黑格尔主义者绝对不是没有意见的。不过,无论黑格尔还是Jakobs,都承认纯粹、事实上的实在性与理性或者说规范性之间的区别。Jakobs的确区别了单纯的、应当具有效力但没有产生实际指引的规范与实际得到承认的规范的区别。特别是对黑格尔来说,法律正好是这样的领域:在其中理性的实在性或是应然的存在应该被实现。因此,康德说的“所有被带有恶意或强权特征的弯路所切断的法基本原理”[86]让正义实现,尽管世界在腐烂,在黑格尔看来不是错误,仅是一种“空话”[87]。 是故,虽然没有敌人刑法要素的理想法治国值得追求,但在现有条件下不能实现,也根本不能对法效力予以保证[88],故Jakobs也会反对理想法治国的概念。在纯粹应然的领域,就此来说,Jakobs和黑格尔确定一致的是,同样,理想法治国最多对哲学家来说是真实的,理想的法治国在天国中观照着哲学家,且因此而塑造哲学家的个人灵魂。就此而言,对法科学者来说,在规范与规范的现实条件之间并没有发生剧烈断裂,因为属于规范的,就会成为事实。反之亦然:一种设置了所有尽可能的手段以维持自身的法秩序,是自我的矛盾:它将不再是法秩序。[89]也就是说,对法规范真实效力条件的形式描述,绝对是属于法理论的,相反,法规范真实效力的具体条件的内容确定并不是法律科学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四)敌人刑法作为例外法 【观点】敌人法作为一种例外法,将一种背离法治国的、不可预测的干预后果合法化。就此而言,它的存在已经与法治国相冲突。[90]在敌人刑法话语中清楚表达的“对期待将要发生的例外状态的高智商兴趣”[91]使得例外状态成了全天候,并且使得该种状态规范化。在这方面,该种兴趣并不愿满足于法律的界限,而是要将其教义学化,它回想起了“精明的精神扰乱者Carl Schmitt,[92]。 【辨析】这种论点没有看到的是Jakobs其实并没有要求例外,他只是将既有的法律标识为法的例外情况,进而去分析其后果。[93]如果例外情况的维持要被认为必要,则至少应该对它设置法定的围篱。围篱的设定条件,是其作为例外情况的标志,即作为市民刑法的例外情况。即便人们不那样来标记例外状况,例外状况也不会消失,更有可能的是,它正好成了惯常的情形有缺陷的法治国通过意识形态上的语词运用而呈现出完美无缺的模样。”[94]例外情况的规范化首先表现在的是,当前行之有效的、为了防御危险而应当最高地适用于危险个体的规则,要适用于所有市民。 在这方面与Schmitt进行对比是错误的,因为对Schmitt来说,统治者决定例外状态,且此种决定通过其统治而实现法律化,但它并不必然是合法的。[95]对那些在合法体系中接受了例外状态但最后却想要取消它的人来说,Schmitt并没有做得太过分。[96]与此相对,Jakobs要求一种合法的程序。[97]敌人刑法是法,因为它将国家、国家的组织、机构和犯罪人联结在一起。[98]此外Jakobs确认通常状态不是此处的例外状态,而是相反。[99] (五)通过敌人刑法的非人格体化 【观点】Jakobs的观念,表明了从启蒙的倒退,对每个自然意义上的人作为人的存在资格,它赋予了人格体的地位。相反,敌人刑法不将人作为人格体来对待,而是作为危险的个体来对待:为了对抗一定类型的犯罪行为,刑法允许对此种个体予以非人格体化。[100]因为,为了预防法律遭受破坏,仅仅从合目的性立场出发而予以对待的那些犯罪人,不再被认为是人格体,而仅仅是被承认为物。[101]此外,Jakobs提出依赖贡献的人格体概念与人的尊严观念整合和配搭在一起。[102]不是作为敌人的存在,这一举证责任绝对不应由市民来承担[103],因为基本法对所有人都规定了不会失去的人格体地位。[104] 【辨析】Jakobs实际是主张一种“以贡献为基础的人格体模型:人格体地位必须通过正派的行为来赢得。”[105]当然,人们在这里必须同样地去回顾Jakobs提出的人格体观念:像康德那样,他将作为屈服于因果法则、由快乐和不快决定的自然物(现象人)的个体,与作为根据规范的指导意见而能够自由地决定的理性物(本质人)的人格体相区别。[106]同时,对Jakobs来说,人格体的存在是一种只有通过社会中主体之间相互承认才有可能的属性(Attribution)。故人格体的存在意味着,义务的承认得到了实现。人格体应该被信任随后能够去履行该种义务。[107]人格体的存在因此是规范的结构:对其他法人格体的、与法一致的行为的期待。每一个人在本质上绝对是人格体,也就是说,履行了义务,人的存在资格就是可能的。谁若只是可能意义上的人格体,对于不同行为的其他人来说却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格体,由于不能从他那里期待得到基本的法忠诚,他也就同样不能要求其他人将他作为人格体来承认。因此,要被承认为人格体,就始终是那些想要那样被承认的人的送达债务[108]。他必须在认知的层面论证,他并不只是根据快乐和不快来行为,他是根据规范的要求而行为。否则,他要求的任何东西都完全没有意义。通常情况下,市民通过提供“至少相当程度足以信赖的法忠诚[109],履行了这样的送达债务。 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体,不仅作为义务的承载者而被承认,同时也被承认为是权利的承载者。谁要是否认某些个体的基本权利,虽然还可以继续地在名义上将其称为人格体,但却没有将其作为人格体来对待,且因此表明他没有将那些个体作为人格体来承认:当刑罚仅仅是犯罪人危险性的防御工具时,人格体实际上就没有在其自身意义上得到承认。就此而言,绝大多数人同样只是承认名义上“永恒的”人格体地位。[110] (六)敌人刑法是对人权的否定 【观点】Jakobs剥夺了法秩序下人的所有尊严,因为他只承认人格体与个体,或者说市民和敌人,却不承认人的尊严和相应的人权。将人作为敌人对待的前提是,他不再是人,而是非人格体,即动物。[111]敌人刑法表明了“人权这一普世观念的断裂”[112][113],因为它对不可侵犯的人权设置了获得普遍承认的条件。[114]这一观念还同时违反了宪法,因为它不仅违反了平等原则(基本法第3条),也与人的尊严不得侵犯(基本法第1条)不吻合。[115] 【辨析】事实上,Jakobs在构想中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放弃人的概念,以及人的尊严和人权概念。[116]这一方面是基于其学说在法科学层面上的定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如下前提:规范与假定不是一回事,规范必须要能够保证法安全。规范不仅仅是要能判断,在现实中必须要能够得到实施。因此,一种仅仅是名义上宣称的或是假定的人权,不能与一种现实的规范相提并论,因为它不能提供法已经提供的东西:对潜在被害人和行为人的行为指引。正如前述,理性的在法中必须也是现实的。人们现在不能否认的是,“普世”人权在许多国家受到侵犯,在那些国家根本没有实现过。全球人权声明在那些国家因为出现了犯罪人而遭到非常成功的反驳。在那些国家,人们既不能以其为行为指引,也不能予以放弃。这让它明显具有假定的特征。故国际上的刑事裁判权并不包含规范效力,而是首先要通过战争状态来证立自身。即是说,军事胜利决定何种法真实有效。谁侵害人权,会受到军事抵抗,而不是由警察通过逮捕令追捕。只有当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没有危险”时,才会在刑法典和刑法秩序上被替换掉。“为了能维护人权普适效力的假定”[117],行为人被回溯地解释成“承认人权”这一法定义务的承载者,就如同法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似的。但是,刑罚仅仅是服务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人们与之作斗争的敌人,不是法意义上有罪责的人格体,故人们也应将保安处分称为敌人刑法。国际刑事裁判权必须要始终适用于战败的敌人。[118] (七)敌人刑法与法治国矛盾 【观点】Jakobs的敌人刑法根据人身危险性来对人进行筛选。这违反了平等原则。法治国甚至会将希特勒、斯大林或波尔波特作为法人格体来对待。[119] 【辨析】Jakobs并不否认,在我们法治国必须同样以法治国方式来对待那些草菅人命的独裁者——尽管只是说,只要他们不再有危险性。虽然在他们当权且因而具有极高的危险性时,也许没有人会主张那样的处置[120]:我们一定不会指责Staufenberg没有等待针对希特勒的法治国程序的启动。欧洲法治国的政治领袖证实了Jakobs的判断,这表明,在杀死本拉登之后相关政治家那些遭人怀疑的反应几乎全部是清晰明确的。[121] (八)敌人性作为决断规定 【观点】Jakobs对市民与敌人的区分,动摇了法治国的柱石:因为是行为人属性,而不是行为,才决定了市民阵营或敌人阵营的归属。[122]如果恐怖组织或犯罪组织成员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能够正当化,则最终会发生“所有人群作为另类人划污名化”[123]威胁。因为谁是敌人的宣告,一直是一种决断规定。 【辨析】这一指责混淆了Jakobs的市民与敌人之分和Schmitt的朋友与敌人之分。[124]对Schmitt来说,朋友和敌人表示人联合或解体的最终目的。[125]这一区别不是法学上的,而是纯政治性的,正是建构政治的根本区别。[126]敌人是现实存在的另类人或外人,在最严峻的冲突场合中,与之可能发生战争。谁是敌人,只是那些作为朋友与某个政治共同体联合在一起的人的规定,这些人根据特定的标准与该共同体联合在一起:语言、宗教、人种等。然而,Schmitt将此种意义上的敌人,即公敌,严格区别于私敌,后者是人们基于不同原因嫌恶的人。[127]就此而言,敌人不是犯罪人,正如朋友与敌人之间的政治区别与善与恶之间的道德区别完全不同。[128] Jakobs认为,敌人刑法的敌人,更确切地说是私敌,就此而言,他受到的待遇,确实异于犯罪人。[129]这种敌人的行为举止应该像同类人一样,社会对他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但这只是社会的期待,因为他持续地让规范期待落了空,没有满足这种要求。故只有在根本上提出敌人刑法,因为虽然存在规范要求,该要求却因外部行为而落空。相反,对Schmitt的敌人,人们既不能提出法律要求,也不能提出道德要求。敌人不是因为其是犯罪人成为敌人,而是因为他是另类人成为敌人。因此,Schmitt认为,敌人不应受到刑罚,仅应被排除。对Schmitt来说,不能仅因敌人是另类人就允许对其犯罪化。相反,对Jakobs来说,不能仅应另类人的另类性就允许对其犯罪化,因为根据他的另类性,如宗教信仰或国籍,他根本不是敌人[130]准确的说,敌人是通过行为举止、职业生涯或与组织的结合关系,“可推知地、持续回避了法”[131]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行为”[132],而不是通过别的如其宗教派别或母语,表明他没有提供对市民行为的最低安全的保障。对自由社会来说,他至少是当下的、不可教化的敌人,是公众之敌而不是国家之敌。[133]因此,Jakobs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只能实行自我排除及使之敌大化:即通过犯罪行为。“自由社会的排除,始终是自我的排除。”[134]因此,对犯罪人来说,通过提供确实可信的、对将来法忠诚的保证,重返市民状态的道路始终是开放的。[135]此外,与Schmitt的构想不同,对Jakobs来说,敌人始终只是部分性的敌人,所根据的则是对他来说何种法忠诚不再能够被期待。因此,敌人从来没有完全地外在于法,仅是从市民法中被排除出来,市民法与敌人的犯罪危险性有关。是故,敌人刑法是“市民地位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减少。”[136] (九)敌人刑法的失控性 【论点】根据敌人刑法,什么才应该被允许? Jakobs对此并没有具体解释,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法科学上的这种自我满足,要么意味着Jakobs认为,与敌人打交道的任何无约束性在敌人刑法下都是正当;[137]要么意味着Jakobs没有尽到仔细思考自己理论的后果的义务,仅仅是“单独地在抽象法学范畴”[138]里来讨论。因为规范理解的话,敌人刑法是“一种致力于取消对刑罚权的所有绝对限制的构想”[139],它在结论中还要给予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以规范上的合法性。[140]因其与Schmitt哲学在精神上的亲缘性,敌人刑法只能以“消灭及抹杀”敌人为目标。[141]因为,在Schmitt看来,统治者只有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时刻才会公开地宣布敌人,以将其消灭。[142] 【辨析】这里显然存在双重的误解。因为无论是Schmitt,还是Jakobs,都认为敌人概念基本上具有保护性功能。对Schmitt来说,假想的战争发生在那些以常规军队作战且相互承认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143]与此相应,敌人不应被消灭,而应被抑制,也就是说,消除他的危险性[144]故Taubes强调指出,法律人Schmitt是希望通过对敌人的定义,“能够避免任何神学上对敌人定义的极端结果”[145]——根据神学上的敌人赋定,敌人始终必须要被消灭。在Schmitt看来,只有通过对下列范畴的明晰区分才能避免那种极端结果:战争与和平、战士与非战士、当然首先是敌人与犯罪人。取消公众与私人之别、军事与民事之别,则会出现一场全面的战争[146],一场取消了敌人与犯罪人之别、人们想要消灭对手的战争。[147]正如Taubes透过Schmitt所发现的,战争不会因其自身被犯罪化而消失掉,反而更可能被引向最坏的形式,因为作为犯罪人的对立者也被剥夺了道德上的资格。[148] Jakobs同样要求明确区分,而且同样是为了要确立界限:对基于罪责的市民刑法与纯粹为了安全的敌人刑法进行区分时,一方面要保护市民刑法免受敌人刑法元素的感染,另一方面要能明确认定敌人:该违法者不是因其实施了与刑罚相当的犯罪行为而被刑罚惩罚,而是因为社会要保护自身免受该违法者的侵犯。法治国应当清楚、毫不含糊地确立二者的界限。Jakobs从描述到规定的跨越,并非要扩张现有的敌人刑法的规定,而是为了介绍一种概念,以用来标识某些特定法律以及它们与规范的脱离,并且要使得该概念变得明确:在这里,国家不再将违法者作为人格体或是市民对待,在这里与规范刑法无关,而是与作为最后手段的例外情况有关。[149]对Jakobs来说,对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对个别法律的抛弃予以标识,正是“例外情况的警告标志”,但是,市民法却把这类规定包含进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规范化。[150]看起来,只要法律——不是事实上的普通刑法,而是预防法——在名义上仍然使用市民刑法这样令人安慰的名字,法治国就没有什么必要反对这种法律的扩张。但是,敌人刑法的标识可以使得严格限制的必要性变得明确。Jakobs要求将敌人刑法限定在必要范围,且要求减少既有的敌人刑法规则。[151]因为敌人本身,始终是人格体,仅仅是为了将来不再发生侵害才允许将其作为敌人。对恐怖分子来说,首先是要剥夺他的“行为自由的权利”[152]。就此而言,敌人刑法的正当根据仅是消极的特别预防,而不是消极的一般预防,因为违法者并不是对其损害他人的倾向承担责任。对那些反对刑讯方法的批评者来说,那一点始终是绝对不值得考虑的。[153] (十)敌人刑法作为术语的相互矛盾 【论点】Schmitt不认为敌人是犯罪人,与其相反,Jakobs走向了一种特别刑法。因此,最后的论点存在于如下问题:用刑法来讨论敌人是否有意义?或者,我们并不一定要去讨论一种预防性的安全法。[154]而对比Schmitt,那正好是存在疑问的:任何国家都制定有战争法,他是作为敌人而不是犯罪人被剥夺资格。就此而言,敌人刑法是术语的相互矛盾,因为敌人并没有对我的义务。从正当性的角度看,敌人不能被刑罚惩罚,只能作为危险来被抵抗。 然而,对Jakobs来说,丧失了市民法上人格体地位的敌人,虽然某些权利(极端情况下甚至是基本的生命权)失去[155],但仍然继续保留了全部义务。因为其违反了义务,在根本上,他仅仅是犯罪人。作为非人格体,敌人要受到某些权利被剥夺的待遇。[156]敌人刑法剥夺其人格体资格。他的政治意图,在这里并不重要,将来可能发生的规范侵害才相关。对Jakobs来说,敌人刑法意义上的敌人与战争法意义上的敌人是有区别的。 对Pawlik来说,首先,这至少表明恐怖分子法律地位的缩减:因为对于恐怖分子来说,战争与和平、战士与非战士、战争与犯罪等等之间的“传统”区分不再适用,战争军事法与刑法之间的传统区分也不能再适用。[157]与恐怖分子作斗争的法律,不如说是“具有战争法要素的预防法”[158]。对Schmitt来说,游击队(der Partisan)是“传统的国家战争的后裔”[159],故pawlik将现代恐怖主义看作游击队理论之后的一贯延续。正如游击队之于Schmitt,恐怖分子之于Pawlik同样也不能被犯罪化。[160]在抵抗恐怖主义造成的危险时,战争法上设定的特别预防目的,更多是通过刑法规范的形式来实现。双方——比如以消极的特别预防与军事对手的交往——仅将目标设定在对手的无害化。[161]战争法意义上的无害化或者说特别预防所意味的,——完全按照Schmitt的看法一-并不是对已经无害化过的敌人人格体资格的剥夺。就此而言,恐怖分子似乎就是战争法意义上所认定的敌人,他也正是那样的被承认[162]只有在普通刑法中,激进的特别预防才是要剥夺人格体资格的。在这个意义上,Jakobs的敌人刑法混淆了刑法和战争法。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正确的,因为对Jakobs来说,人格体资格剥夺的根据,即在于认为敌人是部分地、持续地受快乐及不快所决定,而不是由负有遵守义务的规范来指引。但是,对恐怖分子来说——他们自认为是受到其他规范甚至是更高价值的规范所支配——这一点是否同样成立仍然存在疑问。[163] 【辨析】有两个反对的理由: (1)那些并非用来针对恐怖分子的敌人刑法规定里,到底有些什么?不能再将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危险,类推解释成是军事对手(比如游击队)所造成的危险。 (2)我们真的应该将恐怖分子看作是游击队的延续吗?不仅是因为现代恐怖分子大多缺乏游击队的大地性格,他们很少是单纯要将自己的故乡从占领者那里解放出来,在我看来,二者的决定性区别在于,游击队虽然能够从自己不被标识为战士中受益,但至少是只会攻击对方的战士。相反,恐怖分子大多是在有意识地攻击平民,以散播恐惧和恐怖。[164]看起来,可以认为,Jakobs所说的恐怖分子更有可能被归入到犯罪人的范畴。二者的区别似乎更多是在量上:性犯罪人和黑手党成员一样,只是部分地否认国家的法秩序,恐怖分子则是在根本上否认。故在通常情况下,恐怖分子的潜在威胁更大。但是,这仍然不是使得恐怖分子成为Schmitt提出的公敌意义上的敌人,——也不同于游击队,后者是在战争中事实上的交战一方,因为弱小,只能非对称性地参与战争。 看起来,两种论点之间发生了僵持。但是,很清楚的是,根据敌人刑法来将敌人看成是犯罪人,这只能相对的成立:因为违法者虽然侵犯了规范,但却因此要受到远超过其罪责的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这里出现了Jakobs建议区分敌人刑法与市民刑法的重要原因——Jakobs认为,那些还没有转向为试图直接实施行为的恐怖分子、仅因犯罪组织成员身份而被判决的黑手党成员、已经抵偿其罪责却仍被保安拘留的犯罪人,都应该非犯罪化:他们只是因社会的安全需要却不是因为其罪责而受到十分严厉的刑罚。市民刑法要求的是,他是作为犯罪人而被判决,敌人刑法却清楚地表明了相反的内容:在这里,某个相对来说并无罪责的人,受到了刑罚惩罚,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可以制造出危险。[165] 三、敌人刑法作为调节性观念 在此之后,反对Jakobs“敌人刑法”的基本异议,也许虽然不是被全部清除,但那些异议至少应该是有疑问的。在我看来,与敌人刑法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可能有如下这些: 即便认为所有的预备阶段犯罪化、程序性保障减少等等都完全没有疑问,那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承认这一概念的描述潜能。这一立场意味着,国家对私领域的行为方式施加刑罚,并不是说国家已经将其作为敌人来对待,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最终也是将私领域区分出一个绝不容侵犯的核心领域和一个国家可以调控的领域,并且在私领域内的其他领域里将这样的干预合法化。[166]这一立场虽然在逻辑上经得起考验和前后一致,但是,只要联邦宪法法院宣告它不违宪,刑法的其他侵蚀看起来的就要被合法化。 相反,敌人刑法文献的主流内容是如下这些:作为对刑法进行描述性分析的批判工具,敌人刑法的概念将要并且已经被进一步地、实证性地接纳。[167]不过,从规范的角度理解,敌人刑法概念受到了否定。[168]这一概念是对刑法中某些趋势进行批判性描述的恰当手段,从实证的角度理解,它涉及到术语中的自相矛盾。[169]由此,产生了要求废除所有敌人刑法规定的必要性。我认为这种立场是极端不切实际的:即便那样的要求确实彻底实现,看上去是朝着敌人刑法构想的自我废除方向前进,但是,那样的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充分保证其市民的安全却是令人怀疑的。 人们同意以如下形式对敌人刑法进行规范论述:所有敌人刑法规则都应当保留、相应扩充,并且也以敌人刑法之名加以称呼。在科学上,这一立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拥护,它在政治上也不大可能实现。 人们虽然反对敌人刑法,正如在第2种立场中,从所谓的规范根据出发一样,但却最终赞成在第1种、第3种立场上的、Jakobs称之为敌人刑法的所有措施。那样的批评只关系到“概念的禁忌化”[170]。大致相同的是,当时的联邦总检察长Kay Nehm在2005年法兰克福/奥德河举行的德国刑法教师会议上虽然否定敌人刑法,但却同时要求制定敌人刑法意义上的新的具体规则。[171]他本人在2002年的“911记念会”上,就已经对在面对“受到约束的信息手段、预防性警察手段的各种限制”时,通过“程序性强制手段的适用”,在“侦查中可能发生的不对等舒适性”感到兴趣。[172]这样的一种轻罪最终却导致了敌人刑法要素在现实中的扩张,因为“在所有的要素中,它主要(只)是适用于了着手的氛围”[173]。 人们对敌人刑法的看法在发生积极变化,而不再是持批判态度。因为那样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要肯定对待敌人的、所有能想象到的手段,而是在肯定一种特征:将那些与市民或人格体概念相互矛盾的要素,命名为敌人刑法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敌人刑法概念所需要的现实性,就相当于是一种调节性的观念:人们承认,在任何现实法秩序中都存在着敌人刑法的规则,在其中,有些对于维持法秩序来说是必要的——特别是一定的预备阶段的犯罪化。[174]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规则一直都是合法的,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过分的情况下都是合法的。[175]因此,特别是在普通刑法中对敌人刑法要素分类时,敌人刑法概念存在着调节性功能——尽可能地对其分类,而不是废除。作为调节性的观念,敌人刑法概念至少要确保给必要性规定划出清晰界限,且具有据该界限再次进行批判讨论的可能性。因此,将敌人刑法认为是一种理论,完全是不合理的,这必须要予以避免;敌人刑法是一种不能被消除的现实。[176]现在就又倒过来了:现实被用来产生了概念,尤其是从法治国的视角看,它作为可耻的事实,根据可能性的存在而应该被清除的时候! *本文研究Günther Jakobs饱受争议的“敌人刑法”概念。作者力图以实证方式,将它解释成是一种调节性观念(regulative Idee),而非构成性观念(konstitutive Idee)。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在它的描述功能一作为对某种法律现实予以描述的方式一中来考察该概念;随后分析该概念在规范理解的层面上受到的批评;最后说明本文为何要将该概念作为调节性观念,而不是别的、或多可少更为顽固的解释。本文的中、日文翻译,得到Schick先生书面授权。日文版的翻译,由日本关西大学川口浩一(Hirokazu Kawaguchi)教授完成。敌人刑法不仅在德国刑法学界,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争议,赞同者罕;批评者却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匆忙的误读人士。川口浩一教授多次见到Jakobs教授,曾邀请他到日本关西大学作“敌人刑法”的报告。据川口先生介绍,这篇论文对敌人刑法的解读,得到Jakobs本人的肯定和赞许。本文的译介,也正是源于川口浩一教授建议,由我联系Schick先生商谈翻译计划。 Schick先生非常乐意授予翻译版权。2014年1月10日,译者本人受邀在川口教授主持的关西大学法学研究所“例外状况与法研究班”公开研究会上做了“中国关于敌人刑法的论争”的报告,有幸与山中敬一教授、饭岛畅教授、森永真纲等学界前辈进行对话和讨论,很受教益。相关论文正在修订。同在Pawlik教授门下学习的彭文茂博士亦对本文提出两处意见,已经全部采纳,特别感谢。 |
| 注释: [1]Prantl, Vom rechten Gebrauch der Freiheit, Die diabolische Potenz der Angst Sicheilieit durch Kriegz und Folter? http://www.erich-foomm.de/data/pdf/Prantl,%20H.,%202006.pdf(28.2.2012), S.8. [2]Vgl. Jakobs, ZStW 97(1985),751.有关敌人的文献,参见:Greco, Feindstrafrecht,2010, S.3147。 [3]Domini, in: Vormbaum (Hrsg.), Kritik des Feindstrafrechts,2009, S.279(S.284)-Hervorhebungen im 0riginal. [4]Vgl. Jakobs, ZStW 117(2005),839.关于刑法的警察化(Verpolizeilichung),也可参见:Jakobs, in: Rosenau/Kim (Hrsg.),Straftheorie und Strafgerechtigkeit,2010,S.167(S.172-175). [5]Hassemer, HRRS 2006,130(132):刑事立法者在明显相关的法律中不愿放弃“斗争”(Bek?mpfung)这样的军事性标题,在刑事诉讼法中,尽管规定了无罪推定,仍然在任意称呼行为人,这样的修辞术仅是内衬(Grundierung)。它在结论中仍然谨慎、慎重的使用术语表,现在也在被遵守。 [6]Vgl. Jakobs, HRRS 2006,289(293). [7]Jakobs, ZStW97(1985),751(756):“对主体(Subjekt)的这种限缩,属于一种明显有别于市民刑法类型的刑法:敌人刑法倾向于法益保护,市民刑法倾向于自由领域。” [8]Vgl. Arnold, HRRS 2006,303(309). [9]如果存在着对个人生命、身体自由的现实危险,嫌疑人的一定事况被证实,即该危险是由某恐怖组织发起,为了防御该危险,有必要切断犯人相互之间任何联系及被告与外界之间包括书面或口头的联系,以便相应调查得以进行。 [10]Hassemer, HRRS 2006,130(133)持同样看法:“人们无需去繁琐地解释刑事诉讼法第112条a款中作为羁押原因(Haftgmml)的再犯危险(Wiederholungsgrfahr);它的额头上刻画着罪恶的象征它追求防止犯罪这一实体法目的,而不是程序安全方面的程序法目标。” [11] Vgl. Jakobs, HRRS 2004,88(93). [12]Jakobs, HRRS 2006,289(296). [13] Pawlik, Der TOTorist und sein Recht, Zur Fechtstheoretischen Einoidnung des modernen Tenorismus,2008, S .29. [14]德国《刑法典》第241条规定了胁迫(Androhung):“(1)以对被害人本人或与其亲近者犯重罪相威胁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2)违背良知,谎称即将对被害人或与其亲近者犯重罪的,处与第1款相同之刑罚。”(译者注) [15] Jakobs, in: Eser/Hassemer/Burkhardt (Hrsg.),Die deutscheStrairechtswissenschaft vor der Jahitausendwende, Rückbesmnungund Ausblick,2000, S.47(S.51). [16]Vgl. Jakobs, HRRS 2004,88(94); ders.,ZStW 117(2005),839(840). [17]Vgl. Pawlik (Fn.13), S.30 f.::刑法典第129条b款在结论中还提到了“‘全世界’公众的和平是保护法益”。 [18]根据刑法典第129条a款的规定,尽管被指控的行为方式只具有一般的不法内容,但却允许对人身权进行重大干预,甚至没有羁押原因时也可以审前拘留(刑事诉讼法典第112条第3款),还允许在审前拘留期间封锁外部联系(法院组织法之施行法第31条以下)。参见Pawlik(Fn.13),S.33. [19]Jakobs, HRRS 2006,289(295). [20]Vgl. Pawlik (Fn.13), S.26. [21]持同样看法的还有Hassemer, HRRS 2006,130(136):“刑法上的抽象危险犯中,不法(Unrecht)消失了,为了它仍与刑法相关,罪责(Schuld)变得模糊,行为人的相关能力(Dafur-K?nnen)仍然要为刑法答责。” [22]Jakobs, ZStW 97(1985),751(755). [23]Jakobs, ZStW 97(1985),751(753). [24]Jakobs, ZStW 97(1985),751(761)——原著中强调。 [25]Vgl. Jakobs, ZStW97(1985),751(765).目前的论述都包含了行为人不再可控的“自我能动性的危险”(Gefahr einer Eigendynamik),参见vgl. J?ger, in: Heinrich u. a.(&sg.),Strafrecht als ScientiaUniversalis, Festschrift für Claus Roxin zum 80. Geburtstagam 15. Mai 2011,Bd.1,2011,S.71(S.82),这似乎并没有说服力,正如它只涉及所有行为参与者中的具有罪责能力的人一样。 [26]Vgl. Pawlik (Fn.13),S.26. [27]在形式刑法的意义上,窃听(Lanschangriff)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与市民概念相抵触。参见Jakobs, HRRS2006,289(296.) [28]Jakobs, HRRS 2006,289(295). [29]Roxin将法益定义为:“为了个体的自由发展,为了个体基本权利的实现,为了在此种目标构想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体系”的功能化而必要的“事实(Gegebenheit)或者目标设定”。vgl. Roxin, Stra&echt, Allgemeiner Teil, Bd.1,4. Aufl.2006,§2 Rn.2. [30]对Franz von Liszt来说也是如此,他将“刑罚解释成法益保护”,与黑格尔和康德不同,后者为“反对早期酷虐刑罚,提出为确保个体自由的目的思想的统治。”vgl. v. Liszt, Strafrechtliche Vortr?ge und Aufs?tze, Bd.1,1970,S.126(S.161). Vgl. dazu auch Schunemann, in: Vormbaum(Fn.3), S.11. [31]在性犯罪刑法改革的范围,没有违反性自主的“风俗犯”(Sittlichkeitsdelikte)从刑法典中被删除(乱伦当然是例外的情况)。 [32]Jakobs, ZStW 97(1985),751(753). [33]Jakobs, ZStW 97(1985),751(753). [34]Jakobs, ZStW 97(1985),751(753). [35]Vgl. Jakobs, HRRS 2004,88(89). [36]Vgl. Jakobs, HRRS2006,289(293); den., HRRS 2004,88(90).对康德来说,原则性偏离者(prinzipieüe Abweichler)(即那些不愿从自然状态前往国家状态的人)是敌人,Jakobs首先是从《关于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书中的一处注释推导出来。(Karit, in: K?niglich Preu?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8. S.349).不可教化的犯罪人和恐怖分子,在行为中不承认一个或多个根本规范,在Jakohs看来,他们是在重返该书原处注释所写的自然状态。对康德来说,那样的状态是一种敌人的状态,他在《道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der Sitten)中对此解释说,敌人其实一直是“不正义的敌人”,故允许人们使用“所有受到允许的手段”来保护他的所有物。(Kant, in: K?niglich Preu?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6,S.349 f.)就此而言,Jakobs的解释看上去虽然有所逾越(因为对康德来说更多的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基本上是没有错的。 [37]Jakobs, ZStW 97(1985),751(753). [38]Jakobs, HRRS 2004,88(90):“市民刑法维护规范效力,敌人刑法【……】对抗危险”。Schünemmn (Fn.29),S.17对此表示反对:刑法不是要来维护规范的效力,规范原本只是保护法益的工具。 [39]Vgl. Jakobs (Fn.14), S.49. Vgl. Hegel, Grundlinien derPhilosophie des Rechts,§97=ders.,in: Moldenhauer(Hrsg.),Werke, Bd.7,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1970, S.185::“对法作为法的侵犯”(Verletzung des Rechts als Recht)。 [40]Jakobs, HRRS 2004,88. [41]Vgl. Jakobs, HRRS 2004,88(91). [42]用黑格尔的话说:刑罚是对法的否定的否定,并且指明了法的效力。参见: Hegel(Fn.38-Grundlinien),§97=ders.(Fn.38-Werke 7),S.185 f. [43]Jakobs, HRRS 2006,289(291). [44]Jakobs, ZStW 107(1995),843(844):“刑罚总是在交往的层面持续地重建被破坏规范的效力。” [45]Jakobs, HRRS 2004,88. [46]Jakobs(Vn.14), S.49. [47]Jakobs, HRRS 2006,289(292). [48]Vgl. Jakobs, HRRS 2006,289(289). [49] Jakobs(Yn.4), S.169:“强制使得被强制人非人格体化(depersonalisieren);其他说法都只是花言巧语。” [50]Vgl. Hegel (Fn.38-Werke 7), S.190. [51]Vgl. Jakobs, ZStW 117(2005),839(841). [52] Vgl. Jakobs, HRRS 2004,88(91). S. auch Jakobs (Fn.14),S.51“谁要是想作为人格体来被对待,在他这方面必须要对此作出一定的、认知上的保证,即他本人是在作为人格体来行为。” [53] Vgl. Jakobs, HRRS 2004,88(91). [54]Jakobs使用的带有挑衅性的术语中:敌人刑法必须让那些不能认为是人格体的人“靠边站”(kaltsteilen)。vgl. Jakobs (Fn.14), S.53. [55]Jakobs, HRRS 2004,88(92). [56]Jakobs, HRRS 2006,289(290).关于敌人刑法“今天不存在明显的替代方案”,vgl. Jakobs (Fn.14), S.53. [57]Vgl. Jakobs, HRRS 2004,88(92).也许可以将此种犯罪人与最早由亚里斯多德说的无节制者(Akolastos)或托马斯·冯·阿奎那(Thomas v. Aquin)说的丑恶(Schlechtigkeit)行为者来对比:这种人不承认道德的确定原则,在此方面不可教化,与不自制者(Akrates)和无知者(Unwissenden)正好相反:后者在个案中基本承认道德原则,由于意志薄弱事实上没有根据这些原则实施行为,或者是没有认识到该道德原则或行为的某种(有罪的或是无罪责的)情势。 [58]Jakobs, HRRS 2004,88(90)-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59]Vgl. Jakobs, ZStW 117(2005),839(844). [60]Jakobs (Fn.14),S.54. [61]Jakobs, HRRS 2004,88(93). [62]Jakobs, HRRS 2006,289(295)对于恐怖分子一一根本的对立者——来说,很容易觉得以危险的大小而不是规范有效性遭受的现实侵害作为根据是恰当的,这可以发生在某一犯罪的任何计划中,包括单纯的抢劫罪。这么过分的敌人刑法并非必要,而是恶害。”(Hervorhebungen im Original). [63]这类经验论调同样不是绝对限制,而“只是有限的限制。”vgl. Greco (Fn.2),S.40. [64]在Walter看来,Jakobs和Pawlik关于恐怖主义和刑法的学说“不仅仅是颠倒的,它还是危险的”。(vgl. Walter, Süddeutsche Zeitung v.22.4.2008, S.14). [65]Sauer, NJW2005,1703(1705). Vgl. Schünemann (Fn.29),S.17. [66] Vgl. Gonz?lez Cussac, Feindstrafrecht, Die Wiedergeburtdes autorit?ren Denkens im Sch??e des Rechtsstaates,2007, S.1. [67]Vgl. Ambos, in: Vormbaum (Fn.3),S.345(S.372). [68]Gonz?lez Cussac(Fn.65), S.10 f. [69]Walter, Süddeutsche Zeitung v.22.4.2008, S.14. Dux形容Jakobs的学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恶意(zynisch)、极权主义,“在德国的纳粹主义之后,在科学的讨论中”不可能被再次肯定。(Dux, ZRP2003,189〔194〕)同样的观点参见:Cavaliere, in: Vormbaum (Fn.3),S.315. [70]Bungt in: Uwer (Hrsg.),Bitte bewahren Sie Ruhe, Lebenim Feindrechtsstaat,2006, S.249(S.250). [71]Uwer, in ; Uwer (Fn.69), S.37(S.42):“ An keiner Stellezitiert Jakobs Carl Schmitt, aber an jeder Stelle scheint erbervor.” [72]Walter, Süddeutsche Zeitung v.22.4.2008, S.14. Waldemar Gurdiana提出的“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Kronjurist)称号是否完全准确,是有争议的。纳粹至少指出了除Schmitt本人外并没有特殊利益要由Schmitt来论证合法性,他本人及其思想仍然受到了《黑色军团》(Schwarze Korps)(译注:为纳粹党卫队的官方拫纸)的怀疑,Schmitt在辩护中对此也有所指明。vgl. Schmitt, in; Quaritsch (Hrsg.),Carl Schmitt-Antworten in Nürnberg,2000, S.65.这当然不意味着相反的情况,在Schmitt那里,人们只看到了“智力的冒险家”,而不是他在自我策划。([a.a.O.],S.60). [73]Greco (Fn.2),S.27-30. [74]这方面可以参见Schmitt, Der Leviathan in der Staatslehre des Thomas Hobbes,1982, S.18 und 109. [75] Schmitt, in: Quaritsch (Hrsg.),Positionen und Begriffe Carl Schmitts,3. Aufl.1994,S.227(S.229). [76]通过上述法律,在“行为前阶段即开始考虑因违法者引起的安全问题,为了与违法者作斗争而赋予刑法手段的危机显著扩大”。([a.a.0.],S.1367).是故Ernst Schafer认为这是“德国刑法发展中的拐点”,vgl. Sch?fer, in: Frank (Hrsg.),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Handbuch für Recht undGesetzgebung,2. Aufl.1935, S.1366. Friedrrich Oetker在魏玛时期曾经要求保安法与刑法分离,但在纳粹时期却不再认为有此必要,反而认为可以通过纳粹法证立这两种类型法的联合。vgl. Oetker, in: Frank (a.a.O.),S.1319(S.1364).因此,他认为犯罪人是法益敌人,且从纳粹的刑法观角度认为,“报复并不是因为(行为人)本人的意志,而是为了实现国家权威保护中的法益保护目的。”参见Oetfter (a. a.0.),S.1322. [77]Schmitt, in: Frank (Fn.75),S.24(S.31 f.). [78] H?rnle, in: Vormbaum (Fn.3),S.85(S.100). [79] Taubes, Ad Carl Schmitt, Gegenstrebrge Fügung,1987,S.39. [80]Walter, Süddeutsche Zeitung v.22.4.2008, S.14. [81]Hassemer, HRRS 2006,130(138)现代刑法由此变化成了一种危险防御法。它的话语中充斥着对制造和维护安全的兴趣。” [82]Vgl. Jakobs, HRRS 2006,289(290), [83]Vgl. Jakobs, HRRS 2006,289(289). [84]Greco (Fn.2), S.19. Cavaliere是在说—种纯粹的“描述性的外观”(Schein des Deskriptiven), vgl. Cavaliere (Fn.68), S.323. [85]Saliger, in: Vormbaum (Fn.3),S.203(S.204). [86]Kant (Fn.35-Zum ewigen Frieden),S.378 f. [87]Hegel (Fn.38-Werke 7),S.240. [88]Jakobs, ZStW 117(2005),839(847). [89]一种“以严厉刑罚来实施独裁的秩序”不是规范的秩序,而是权力的统治。vgl. Jakobs, Norm, Person, Gesellschaft,2. Aufl.1999, S.54.故极权国家不会建立起人格体的秩序(personale Ordnungen),只会发展出统治个体的手段,如Jakobs(a.a.O.),S.77. [90]Saliger(fn.84),S.218 f.:它甚至具有极权的特征,因为通过敌人刑法,例外状态法(das Recht der Ausnahme)得以以体面的方式、伴随着不可预见的干预后果来进行^就此而言,不容再次争议的是,在法治国家中究竟是否能够存在这样的例外法(Ausnahmerecht)。例外状态法的存在前提,也是受到容许的前提,是它的适用类型及范围问题。 [91]Di Fabio, NIW2008,421(423). [92] Di Fabio, NJW 2008,421(474)-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93]故稍后在2006年,Jakobs认为,被宣告违宪的《航空安全法》第14条第3款,即允许在恐怖袭击的情况下射击载有未参与恐怖袭击者的飞机,这一规定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即,当恐怖分子引发例外状况时,在“必要”的范围内,针对无辜的市民,它可能会没有禁忌地强制适用“突破体系性的”(system sprengende)的权利剥夺和非人格体化。vgl. Jakobs, ZStW (2005),839(848.) [94]Jakobs, ZStW 117(2005),839(851). [95]因为决定例外状态的统治者,“处在规范有效的法秩序之外,但仍然属于该法秩序,因为他才有权决定是否要在总体上来中止执行宪法。”Vgl.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9. Aufl.2009,S.14. [96] Vgl. Schmüt (Fn.94), S.13:“因为通常的规范,正如它所表示的通常有效的法律规范(Rechtssatz)那样,绝不可能规定绝对的例外情况(absolute Ausnahme),.也不可能彻底证立真正例外情况的存在判定。 [97]敌人刑法仍然是法律,因为它与“一种经由特定规则推定出的(regelgleitetes)且因此非自发性的、非感性的行为”有关,vgl. Jakobs, HRRS 2004,88. Vgl. auch Jakobs (Fn.14), S.53. [98]对此表示反对的有Schmitt (Fn.74), S.228:统治者创设(schaffen)的是勿宁说是法。“在危险的时候,为了保护法免受最坏的滥用,元首根据其作为最高审判权领主(Gerichtsherr)的元首地位,直接创设了法”。 [99]Anders Schmitt (Fn.94), S.13. [100]Vgl. Crespot in: Vormbaum (Fn.3), S.385(S.393). [101]Vgl. Greco (Fn.2),S.52. [102] Vgl. Bassemer, HRRS 2006,130(138). [103]Saliger(Fn.84),S.217:“因为可信赖的法忠诚其不明确的送达债务(diffiise Bringschuld),在错误行为(Fehlverhalten)中要被排除,从而导致市民完全放弃对安全问题的参与管辖(Mitzust?ndigkeit)。市民不仅对国家要负有不得实施可罚行为的责任,还必须要提供足可信赖的——深入广泛的——法忠诚,以保证本人不会作为危险源被消灭。” [104] Vgl. Neumann, in: Uwer (Fn.69),S.299(S.313). [105]Neumann (Fn.103),S.310. [106]Vgl. Kant (Fn.35-Metaphysik der Sitten), S.239-242. [107]Jakobs, ZStW 107(1995),843(866):作为人格体的存在,意味着其他人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最常见的是对法的尊重。 [108]送达债务(Bringschuld),即需要在债权人处所被履行的债务。——译注。 [109]Jakobs, HRRS 2006,289(293)-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110]在这里尤其是《航空安全法》第14条第3款(§14Abs.3 LuftSiG.)的安全。 [111]Ambos (Fn.66), S.369. [112] Pulitano, in: Vormbaum (Fn.3),S.269(S.270). [113] Vgl. Crespo(Fn.99),S.394; Ambos (Fn.66),S.376. [114]Cavaliere (Fn.68),S.326 und Neumann (Fn.103),S.313. [115]. G?ssel, in: Vormbaum (Fn.3),S.43(S.50 und 55). [116]Vgl. Heger, ZStW 117(2005),865(887) und Jakobs(Fn.88), S.5. [117]Jakobs, HRRS 2004,88(95). [118] Vgl. Fronza, in: Voembaum (Fn.3), S.413(S.417 f.).它应该在道德的层面将政治军事上的失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法化。 [119]G?sse/zitiert nach Heger, ZStW 117(2005),865(883). [120]Vgl. Jakobs, HRRS2006,289(289). [121]另一位联邦总理默克尔就是这样祝贺美国杀死本拉登的。这会表明的是,恐怖行为不会总是不用赎罪,它还要服务于对其他恐怖分子的遏制。同时,它会成为一个重要标志,并且是危险的切断。这里最终产生了以军事手段进行的消极的特别预防及消极的一般预防。(http://www.bvmdesregierung.de/ Content/DE/Mitschrift/Pre8Sekonferenzen/2011/05/2011-05-02-merkel-osama-bmladeix.html,28.2.2012) [122]在Ambos之后,Jakobs也认为首先是针对来自外来文化的他人。” vgl. Ambos(Fn.66),S.364(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123] Greco (Fn.2),S.53.对市民与敌人的区分因此成了“向丛林的退缩”(Gonzalez Cussac[ Fn.65],S.23),处在丛林之外的,是与我们不同的人:“被害人化的群体,如移民、流浪者、毒品依赖者以及甚至是外国人”,(a.a.O.,S.35)-(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Vgl.anchThiée, in: Uwer (Fn.69),S.195(S.224). [124]相反,Greco已经提出批判性的反对意见,这里只是“表面上的术语一致”。把Schmitt与Jakobs划等号(Identifizierung),“远远低估两位法学家思想的原创性及体系完整性。” Greco(Fn.2),S.26,27.(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125]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1963,S.38.带有一篇前言及三个结论的1932年的文本。 [126]Schmitt (Fn.123), S.26. [127]Vgl. Schmitt (Fn.123),S.11 f.因此他赞美罗马法,因为它知道“区分敌人(Feind),公敌(hostis),强盗(R?uber)与犯罪人(Verbrecher)”。vgl. Schmitt, Der Nomoader Erde im V?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 ,4. Aufl.1997, S.22. [128]Schmitt (Fn.123), S.27. [129]Vgl. Jakobs, HRRS 2006,289(294). [130]当Walter将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囚禁称作法治国的丑闻时,Jakobs是绝对同意的。vgl. Walter, Süddeutsche Zeitung v.22.4.2008, S.14. [131]Jakobs (Fn.14), S.52. [132]Jakobs (Fn.14), S.52. [133]Jakobs, HRRS 2006,289(293):“今天只能(将敌人)理解成为是原则性的对立者,而不(仅)是现有统治的对立者,他更多地要被认为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社会的敌人。……谁若是已经成为稳定的犯罪结构的一部分,则对他来说基本没有希望的是,尽管存在单个的犯罪行为,可是为了纯粹的幻想,或是为了‘无尽的、反事实的’的期待,人们仍然能够找到共同的折衷办法。”敌人只不过是不承认法秩序,且通过其行为来表明了这一点的人。因此,谁是敌人的判断,不是先验的(a priori gef?llt)(Crespo[Fn.99],S.400),实际上是后天的(a posteriori)。 [134]Jakobs, HRRS 2006,289(293);自我排除当然不意味着敌人能够决定他何时被排除,何时不被排除,这一点始终是由社会来决定的。社会同样要决定的是,在多大的范围内关押或释放敌人,它也没有免除敌人不得实施犯罪的义务。vgl. Jakobs, HRRS2006,289(293,294)。对此持批评态度的是Ambos (Fn.66), S.362.稍后,Aponto发现在哥伦比亚后期存在的但并没有减少的敌人刑法经验:“敌人始终是人为设计的敌人。一直都存在对敌对性和敌人的判断。……认为敌人就是那些也会同样的人,这完全是天真的想法和蛊惑人心的宣传。”Vgl. Aporne, HRRS 2006,297(300)。 [135]Jakobs, HRRS 2006,289(293 f.):“通过行为的改变,敌人可以再次成为市民。社会不是不让敌人“进入”;敌人是对‘加入’(Hineinkommen)进行了自我设障,因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送达债务,也就是说,敌人没有努力让自己的法忠诚行为可以被预测。”恐怖分子也会悔恨,他对自己行为中不法性的认识,这些都能够表明其作为恐怖分子的根据,恐怖分子不是必须始终要被认为是人格体(Person)。(vgl. etwa Walter, Süddeutsche Zeitung v.22.4.2008, S.14),通过敌人刑法,任何事都不再是不可能的。 [136] Silva Sànchez, ZStW 118(2006),547(549)-(Hervorhebungim Original). [137]Malek在这里担心“真正的、可怕的答案”,“wahrhaft gespenstische Antworten”,vgl. Malek, HRRS 2006,316. [138]Ambos (Fn.66), S.370. [139]Greco (Fn.2),S.53. [140]Vgl. Malek, HRRS 2006,316(317). [141]Vgl. Bung(Fn.69), S.262 und Ambos (Fn.66), S.357. [142] Vgl. Uwer(Fn.70), S.43. [143]Schmitt, Theorie des Partisanen,1963, S.87:“敌人并不是从任一根据或因其无价值就必须要被消灭。敌人存在于我自己的层面。” [144]Vgl. Clausewitz, Vom Kriege, Bd.1,Berlin 1832, S.3 f. [145]Taubes (Fn.77), S.7. [146]Pawlik (Fn.13), S.20. [147]因此,“诉诸战争权”(ius ad bellum)使得战争双方相互承认成为可能,使得战争的非犯罪化成为不可能。因此,任何敌人都是正当的(gerechter)敌人。“承认一个正当的公敌(justushostis)的能力,正是所有国际法的开始”。vgl. Schmitt(Fn.125), S.22. Dagegen Kant (Fn.35-Metaphysik derSitten), S.349 f. [148] Taubes (Fn.77),S.50 f. [149]Jakobs, HRRS 2006,289(294):敌人刑法同样不是为了消灭殆尽而可以没有规范守则,它是精明(klug)管理的法治国家中一种最后的手段(ultimaratio),是在被有意地作为例外情况(Ausnahme)来适用,不会特别频繁地适用。要实现这一自我决定,首先当然有必要知道的是,在敌人刑法规则面前,人们‘手中握有什么’。这可能是出自善意,但肯定不是好的构想,所有权利都始终是相对于每个人的权利,因为不允许是其他情况,在对这种情势简单描绘中,(或多或少广泛的)敌人排除掩盖了敌人权利涉及的内容,以及例外情况(Ausnahme)的警示标志。”(Hervorhebungen im Original).因此,就此而言,智慧(Klugheit)不是在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t)意义上来理解,而是要在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意义上来理解。 [150]Polaino-Orts因此将敌人刑法的相关内容称为是“刑法最后手段的最后手段”(“ultimaratio der ultimaratio dea Strafrechts”)。Polaino-Orts, in: Heinrich u. a.(Fn.24),S.91(S.111). [151]Vgl. Jakobs, HRRS 2006,289(297).因此他在1995年要求删除刑法典第267条、130条、131条、140条规定的前阶段的犯罪化(Vorfeldkriminalisierungen)。vgl. Jakobs, ZStW 107(1995),843(858)。哥伦比亚的刑事法院判定在Jakobs的敌人刑法基础上确定的法律规定是违宪的,这一事实被某些批判者简单地认为没有意义。同样的见解比如Ambos(Fn.66),S.374. [152]Jakobs, ZStW 117(2005),839(847). [153] Vgl. Jakobs, ZStW 117(2005),839(849).敌人刑法“一定不能认为是从现在开始允许所有手段,认为它还包括没有限制的行动;可以认为,敌人也希望自己具有潜在的人格体性(Personalit?t),在与其做斗争时才不会允许赶过必要性限度”。Vgl. Jakobs (Fn.14),S.51. [154]本人对此的看法是:“人们喜欢问的是,为什么这种安全(Sicherung)要称为敌人‘刑’法(Feincdstrafrecht),当它仍然是关系到一种‘安全法’(Sicherungsrecht)的时候。命名的根据是由立法者决定的,他将这种安全措施(Sicherung)规定成刑法的形式”。vgl. Jakobs, HRRS 2006,289(294)-(Hervorhebungenim Original). [155]Jakobs sieht将基本权利的剥夺认为是非人格体化的最高可能等级,在我看来这是有道理的。与此相对的是,针对正在使用的、仅载有恐怖分子、以杀害平民为目标的飞机,巴伐利亚宪法法院认为,击落这样的飞机,是对被击杀恐怖分子人格体性的承认:BVerfG, Urt. v.15.2.2006-1 BvR 357/05, Rn.140 ff. [156]Jakobs, HRRS 2006,289(293):“他的义务并没有减少(当在认知的层面上,义务的履行不再能够被计算时也是如此),否则他就会因为没有违反义务而不是犯罪人。只要他的权利被剥夺,他就——符合定义地——不会被作为法律上的人格体来对待。” [157]Vgl. Pawlik (Fn.13),S.22. [158]Pawlik (Fn. 13), S.47. [159]Pawlik (Fn. 13), S.42. [160]Vgl. hierzu: Schmitt (Fn.141),S.87. [161]Vgl. Pawlik (Fn.13),S. 26. [162]Vgl. Pawlik (Fn.13),S. 40 f. [163]Jakobs此当然是表示反对的:Jakobs, ZStW 118(2006),831. [164]Pawlik本人的看法:恐怖分子的策略正好在于取消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恐怖分子为什么也应该享受这一区别的优待?参见Pawlik (Fn.13),S.23。 [165]对此从未曾确认的是,敌人刑法“自身使用了这一概念,表明了自己是法律”。Vgl. Jakobs (Fn.14),S.51. [166]Vgl. G?ssel(Fn.113), S.45. [167]Vgl. H?rnle(Tn.78), S.85-105. G?ssel认为这一概念是具有肯定能力的,只要它用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目的。vgl. G?ssel(Fn. ll3), s.45.故甚至连刑事辩护协会都为了标识出保安处分的改革目的而使用“敌人刑法”概念。(http://www. Strafverteidigervereinigungen. de/Matmal/Stellungnahmen/StellungnahmeDiskussionspapierSVOkt2010. pdf[28.2.2012], S.4).对此持批评意见的有Kritisch dazu vgl. Saliger (Fn.84), S.210. [168]Neumarm (Fn.103),S.314:“‘敌人刑法’的概念带有正面的含义,当它作为分析范畴,或者以批评意图,用以谴责法秩序时,那样的法秩序将犯有刑事罪行的市民不是作为犯有刑事罪行的市民,而是作为‘敌人’来对待。当这种概念用做肯定性意义时,就会陷入危险的政治性修辞中,因为它提出的建议是,为了与敌人做斗争,(近乎)所有的手段在刑法上都会受到允许,且因为“敌人”的定义,正如在历史教训中学会的,在国家对人群的迫害中是不会受到控制的。” [169]Meli?, ZStW 117(2005),267(268). [170] Melia, in: Vormbaum (Fn.3),S.1(S.9). Vgl. dazu kritisch: Prittwitz, in: Vornbaum (Fn.3), S.169(S.179). [171] Vgl. Heger, ZStW 117(2005),865(886 f.). [172]Nehm, NJW 2002,2665(2670). [173]Kant (Fn.35-Zum ewigen Frieden),S.395. [174]在这个意义上,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是“两种几乎完全不会纯粹地、各自实现的观念类型”,因为在形式上,恐怖好还是会作为人格体来被对待,就此而言,他在程序法上还是被认为是市民的、有罪责的,且在另一方面,在市民的判断时会被认为是危险防御的要素。它关系到的是在“刑法的内在联系中两种同时进行的趋势”。vgl. Jakobs,HRRS 2004,88(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175]Jakobs, HRRS 2004,88(95). [176] Fiandacas, in: Vormbaum (Fn.3), S.21. |